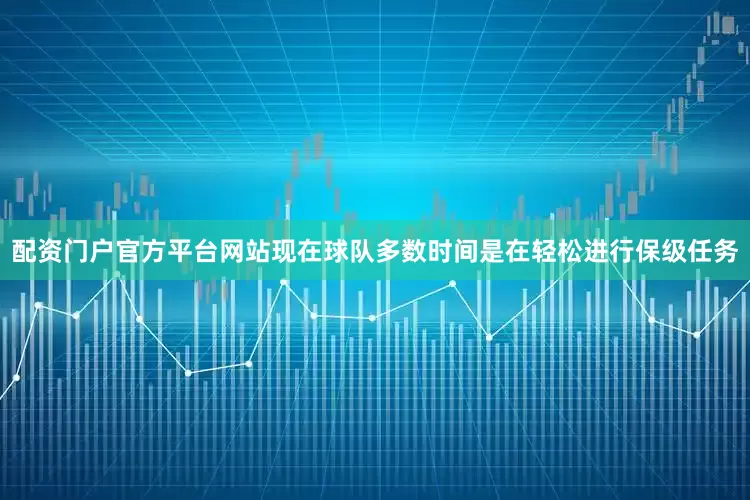一个国家正在消失?16000人的城市仅剩8人,基辅的未来在哪
外喀尔巴阡山脉的风,如今吹过的拉希夫市,恐怕带起的只有尘土和寂静。这里曾经是个一万六千人安居乐业的小城,现在呢?你走街串巷,可能碰到的活人,用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——只剩下八个。
这不是什么电影里的末日场景,是乌克兰西部正在上演的真实画面。当地人说起这事,眼神里全是茫然。工作机会?早就没了。年轻人要么被一张征兵令带走,要么拖家带口逃往了欧洲。留下的,都是些走不动的老人,守着一座空城,在荒芜里硬撑。
这种空心化的景象,像病毒一样在乌克兰的版图上蔓延。联合国那边给出的数字冷冰冰,三年里,六百八十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。这些人可不是简单的数字,他们是工程师、医生、教师,是一个国家赖以运转的血液和筋骨。
更要命的是内部的“失血”。乌克兰自家的一位经济学家,叫阿列克谢·库什奇,他算了笔账,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。从2022年开始,这个国家每年自然减少的人口,高达三十三万。

怎么个减法?一年里头,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大概十七万,可撒手人寰的却有五十万。这就像一个水池,进水管细得像根针,出水管却开得像个消防栓,池子里的水能不干吗?
库什奇把这笔账算得更细。他说,这十七万新生儿里,将来长成姑娘的,顶多九万。就算这些女孩一个都不少地活到能生娃的年纪,一个都不往外跑,按照现在低得可怜的生育率,她们这代人,最多也就能生下五六万个孩子。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下一代的人口基数,直接被腰斩还要多。前议员奥尔哈·博戈莫列茨曾经悲观地预测,说乌克兰民族可能在一百八十年后消亡。库什奇听了直摇头,他说哪用得着一百八十年,咱们这代人就能亲眼看到终点线,这个世纪末就是大结局。
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,而是已经越过了那条无法回头的线。可笑的是,社会上一半人还处在迷茫当中,另一半人压根就没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正在塌陷。

人往外跑,里头还自己跟自己掐起来了。为了躲兵役,大白天的街上几乎看不到壮年男性,他们像惊弓之鸟,生怕撞上街角游荡的征兵人员。这种猫鼠游戏,时常会擦枪走火。
一些极端的声音更是火上浇油。有个叫德米特里·科尔钦斯基的家伙,公开叫嚣,说征兵办公室应该直接开火“教育”那些不听话的。这话听着像疯言疯语,可沃伦地区真就发生了居民和征兵队的大规模冲突,一位老人被打伤,军方回头却轻描淡写地否认了。
外部的战火还没停歇,内部的裂痕却越撕越大。一位叫拉里萨·尼索伊的女作家,居然公开提议,要让孩子们从小就“鄙视那些讲俄语的同龄人”。这种煽动仇恨的言论,简直是在国家的伤口上撒盐。
哈尔科夫,一座英雄城市,绝大多数居民都讲俄语。他们顶住了最猛烈的炮火,可当他们逃到西部寻求庇护时,却要面对高昂的房租和语言上的歧视。一位博主奥列克桑德·帕鲁博克就发出了灵魂拷问:他们宁可去求助波兰人、德国人,也不愿再看自己同胞的冷脸,这样的国家,还谈什么团结?

追根溯源,很多人把这一切的起点,指向了2014年的那个冬天。独立广场上燃起的火焰,似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,释放出了谁也无法控制的恶魔。人口危机、社会撕裂,都是从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。
想当年,苏联刚解体那会儿,乌克兰可是个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的东欧大国,是世界粮仓,工业基础雄厚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如今的景象,真叫人唏嘘。人口的断崖式下跌,带来的不仅仅是兵源枯竭,更是一个国家长远的经济和社会灾难。
没人干活,谁来创造财富?没人交税,养老金从哪儿来?当一个国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,它的未来也就被一眼望到了头。这种慢性死亡,有时候比战场上的炮火更让人感到绝望。
基辅的决策者们,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往前一步,是需要填补无底洞般的兵员缺口;往后一步,是整个民族香火断绝的深渊。他们似乎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,要么在沉默中屈服,要么在逃亡中寻找一线生机。
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,但人心的裂痕,需要几代人去弥合?流失的人口,又拿什么去吸引他们回来?一个没有了年轻人的国家,即便赢得了战争,守着一片空荡荡的土地,又有什么意义呢?这恐怕是比任何军事战略都更让人头疼的问题。
我的看法:
这场悲剧的核心,已经不单单是战场上的胜负了。一个民族的存续,远比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为根本。当内部的仇恨烈火烧得比外部的炮火还要旺时,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为之流血时,真正的危机就已经降临。战争或许会摧毁建筑,但这种由内而外的自我消耗,正在一点点抽空这个国家的灵魂。
利好优配-证券配资最简单最准方法-十大配资公司排名-配资港股一览表 今日大盘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